- 首頁
- 作家動態
- 另眼看書
橫斷時空的存在~評《沙瑪基的惡靈》/唐墨
2016/6/3 上午 09:30 資料來源:唐墨

圖片來源/唐墨
又是本格。
我對《沙瑪基的惡靈》(以下簡稱《沙》)所升起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形式流派上的分類。長期研究演歌,因為演歌的介紹而認識了松本清張的《翻越天城》和水上勉的《飢餓海峽》,導致我對推理小說的第一次經驗,其實是很社會派的。可以說,從此對社會派的寫作風格與內容訴求較為傾心,甚至是偏心;但就是如此,推理小說才會這麼可愛,既讓人不停地思索世界動盪與社會變遷,同時也能翻轉出最新的殺人詭計和殺人舞台。我想,不管任何流派都一樣,不變而且不斷想要探討的問題核心,是一體之兩面,即:刀刃下的血腥,刀柄上的原因。

‧《飢餓海峽》電影改編自水上勉作品,真實再現日本戰後混亂年代的貧困
《沙》所吸引我的,是關於沙馬磯頭這個古地名的運用,兩年前為了研究台灣的海盜史,寫了一部尚未出版但已獲獎的歷史小說,當時就讀過大量的台灣沿海史料,包括信史與野史,甚至是鄉野傳說,所以對於這個題材非常感興趣。小說《沙》中所使用的「屠島傳說」,其實在當時是個見怪不怪的現象。地理大發現以來,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以及最後發跡的英國,為了爭搶香料,謀奪領土與財富,屠島屠村都是很常有的。譬如西班牙曾在一夜之間殺盡一萬多名滯留馬尼拉灣的海外華人,只因為那些海外華人不被明朝承認,沒有國家的保護,成了海上的孤兒,一旦利益發生衝突,這些海外華人的寶貴生命很輕易地就會被犧牲掉。只要是沒有發展出主權的政府,就會成為東印度公司屠殺或剝削的對象。
不得不稱讚台灣早期剽悍的原住民,至少在遊記如《東蕃記》、《原住民概述》等文獻中,一再地讓各種外來殖民勢力吃鱉;鮮為聽聞原住民在抗外的戰役中被殲滅,反倒是文化侵略與生存空間萎縮的問題較為嚴重。小琉球的烏鬼洞傳說,是原住民被屠滅的少數案例之一,《沙》運用這個傳說,塑造出小琉球的禁忌與神秘感。克麗絲蒂《一個都不留》、橫溝正史《女王蜂》和《獄門島》等作品,無獨有偶都是和島嶼有關係的案件,而且案件中都以歌謠、俳句、或口語傳說等文本為貫串犯行或解釋犯行的線索,這些文本讓「孤島」這個空間投射出一種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心理狀態,很多在島上發生的事情,會因為潮汐波濤、海風暴雨等各種異於一般生活空間的自然環境現象,而被過度解讀成有意義或甚至是有主宰的可能,那麼故事很容易就會變成推理當中帶著一點驚悚的元素在裡頭。橫溝正史也曾說過,「有鬼也不錯」的本格小說,便因為空間的置換而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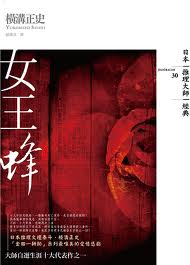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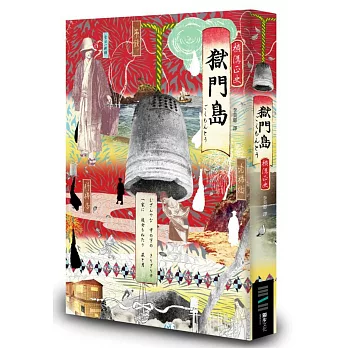
《沙》就是這樣的一部作品。首先殺人必有動機,較諸推理小說當中,不外乎財情仇怒四種殺機。財殺情殺都是人之所欲,難以避免,更是埋下仇殺或怒殺的遠因,可以說是殺意的根源;而沉寂預謀最久的是仇殺,但也是最有機會勸退感化的一種殺機;動之一瞬收之一瞬的怒殺,連懊悔都來不及,遑論阻止。以一樁孤島殺人事件來說,因為得把所有當事人網羅到島上,所以源於名利或情愛而醞釀預謀的仇殺,應該是孤島殺人的基本定調,《沙》當然也脫不了這樣的框架,但是《沙》所構造出來的兇手,是一個惡靈。一個潛藏在島上,出手迅速,而且深諳島上傳說的惡靈。也只有惡靈,尤其地縛靈,可以這樣跨越時空地存在,一切存活的意義就只是為了復仇。
在閱讀《沙》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二個強烈的企圖心。第一,這不會是作者的最後一部作品,或者在這之前已經有試寫的前傳了。小說中的偵探,依循著兩人小組的模式在推動劇情,我也曾試過三人小組的偵探,但那樣的敘述聲音是很亂的;可以說,兩人小組的功能,其實就是把讀者分為破得了案跟破不了案這兩種族群,當讀者自認自信很夠的時候,就將自己代換成較為聰穎的福爾摩斯或白羅;如果讀者純然地想要當個聽故事的人,大可以把自己視為和華生或奧麗薇夫人同一個化身。《沙》的兩人小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們沒有主從強弱的關係,必須視場景、視情況或甚至視交談的對象而定。如果是野外偵查與搏鬥的事件,應該是李武擎負責;面對法庭推理或資料搜尋的工作,唐聿則較為拿手。而這個組合帶給讀者的樂趣,即是在不經意的橋段當中,浮現兩人之間微腐的關係。大概天底下所有的好哥兒們,其實都是互相意愛而在一起的,無須讀者亂點鴛鴦譜,小說內文就不斷地暗示這是可能發生的危機(?)。
《沙》的第二個特質,在於真實地景的融入。這一點可能和旅情推理有點微妙的關係,總之,台灣當前已出版的推理小說中,真實地景的使用並非敘述的重點,更不會是賣點,但《沙》做到了在地化書寫的功夫,而且小說中很多場景都不是從網路搜尋遊記就能抄得來的,足見《沙》的作者應該在那裡做過深度的勘察。雖然,一個地景的書寫並不能完整代表推理小說的在地化,但有這樣的開端,加上作者的企圖心,其實不難期待綠島觀音洞、宜蘭龜山島也被寫成推理小說。我曾在蘭陽文學獎獲獎的推理小說,就是挪用了草嶺古道的地景以及小說《翻越天城》為模型,在那樣的書寫中,因為和土地有了結合,所有想像的過程都是快樂的。我很能感受到作者對小琉球巨細靡遺的熱愛,是文字也無法承載的。
小說《沙》也並非完美無瑕,幾個在我讀後的感想是,原住民的傳說雖然被端上桌了,但是原住民的聲音並未真正被聽見;我想,小琉球還是有原住民的,我其實很想在《沙》中看到原住民角色的登場,用他們的角度來詮釋他們的血淚史。幾個簡單的問答與對話,可能就會翻轉讀者對於某些歷史事件的定見,即是新歷史主義一再關注的多樣性:
傳統的歷史眼光是單聲道的,它把原本存在的鬥爭掩蓋起來了。它認為即使是擺在那裡、似乎一成不變的歷史事實,它們實際上不僅是我們所考察的那個歷史階段中某一個特定社會集團與其他社會集團衝突的結果,而且也是歷史學家自身意識形態構成的產物(註1)。
再者,偶爾被提到的王船祭,不也是極好的題材嗎?但是看完了《沙》之後,我認為李唐二人要回到小琉球來破案的機率應該不大了,也就是說這個題材被作者發現,但卻沒有獲得採用。以我個人淺見,這是極為可惜的事情。而一些人物對話的模擬,似乎不脫北方語言長期宰制的餘毒,譬如像漁夫林思源用「我那婆娘」來稱呼自己的妻子,是否為一介小琉球漁夫的真實情形?難道不會是用「阮牽手」來稱呼嗎?
諸如此類的一些小遺憾,可以說是同為小說作者的互相勉勵,也可以視為大學同窗的敦促,更可以當作我個人的牢騷強解,一笑視之。畢竟那都是不干擾閱讀樂趣,也不影響推理小說情節的支微末節,擺脫這些細部處理的影響,《沙》不失為一本介紹台灣地景的推理小說。盛讚為東野圭吾也無法複製的推理小說,就是因為這個得天獨厚的台灣地景吧!
註1:盛寧,《新歷史主義》,頁95。
作者簡介
林恕全,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碩士,筆名唐墨。
十五歲時,靠著聽演歌的方式自學日文。由於興趣廣泛,大學時代擔任崑曲社長,從孫麗虹老師學小生;又參加日文歌唱比賽,靠演歌獲得全校冠軍;平常是咖啡講師,隨入行廿年的母親開班授課;長期關注於歷史小說和推理小說的創作,出版過歷史小說和談論表演藝術的散文集。對京都也對文學逐漸產生興趣,始自林文月的《京都一年》以及她偉大的譯作《源氏物語》;而寫作的啟蒙,是大學的老師、後來研究所的指導教授廖玉蕙。推理小說〈山婆假燒金〉獲得第十二屆台灣推理作家協會徵文獎決選;[黑色歌仔簿]獲得國藝會補助、[黑色折傘]獲得台北文化局台北文學獎年金補助。
專欄網站:京都千面相
延伸閱讀
徐承義:虛實空間的島嶼拼圖──《沙瑪基的惡靈》導讀
推動無核家園的重要一步 台灣能源新救星就在小琉球!只不過……
秀威和推理小說相關的專區
推理小說:挑戰不可能犯罪與破解
秀威和旅行相關的專區
旅行地圖:把世界裝進人生行囊
今日人氣:0 累計人次:13 回應:0
您可能有興趣的文章